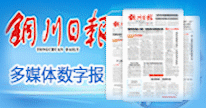悦读铜川 | 铜川民谣
铜川民谣
刘新中
某一个日子,准确地说已经快四十年了,全国群文系统轰轰烈烈搞民间文化集成资料搜集工作,铜川群众艺术馆的几个同事到农村采风,我心血来潮跟了去。山塬上,一个应约的村民老汉坐在地头,说着关于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出现的新民谣:“单干黑,互助明,人民公社上地满天红,责任制上地不分黑和明。”此时,一队结婚迎接新娘的队伍走过,毛驴头上扎着红绸,喇叭欢天喜地地吹着,还有人放着鞭炮。触景生情,豁牙的村民老汉突然话头一转,念出一首据他言是他爷爷辈的爷爷辈传下来民谣:“撒炕东,新郎新娘心相通,有文有武有前程,婆婆心里暖烘烘;撒炕南,新郎新娘心相连,日子越过越红火,有吃有穿又有钱;撒炕西,新郎新娘莫相欺,你恩我爱永不离,白头到老好夫妻;撒炕北,吉祥如意放光辉,夫妻恩爱深似海,棒打鸳鸯不离飞;撒炕中,叫声新娘仔细听,今日撒出好夫妻,来年抱个胖小子。”
正是春天,和煦的风暖暖的,迎娶的队伍拐过一个山峁,去了。只有喇叭声还余音袅袅,和应着豁牙老汉一字一句的吟唱。我的心里突然涌上丝丝感动,那一刻,关于土地,关于这片土地上的民谣,恍然间似乎有了些许顿悟。
民谣是民间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老百姓最原生态的所思、所想、所追求、所倾诉,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化的基础。早在3000多年前的西周时期,官府就有采诗、采风制度;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就是在民谣的基础上诞生的。
民谣大多通过“口传心授”的形式保存,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了解一个时期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生活与愿望表达,民谣无疑是一个不错的渠道或媒介。
我想起了一件往事。
1973年,我被分配到一家瓷厂烧窑。一天封窑,一个老师傅用黄泥巴捏了一个圆柱体,后面立着一个人模样的东西,看左右无人,嘴里念叨了几句,那时年轻,耳朵好,听得清清楚楚:“猪头供上哩,窑火烧旺哩,一窑的碗,一窑的缸,一窑的粮食堆满炕。”
据说,人形物是窑神,烧窑时,师傅不停地从火孔看那个黄泥柱和那个人形物,到了一定温度,黄泥柱烧软了,融化了,人形物就露了出来,也就是说窑神露面了,窑到火候了,该停了。
早年间,祭拜窑神是郑重的,点火之前,窑工们净手焚香,心灵纯诚,口中念念有词。只是到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还有祭拜窑神这类劳什子,并且祭拜窑神的歌谣被流传下来,我有些目瞪口呆。
很多年后,我才明白,这是一种顽强而固执的文化存在,是一方土地延绵不绝的文脉。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过:“这是一个考古学家和文物工作者不太提及的话题,科学不相信迷信,科学与迷信相克,但如果谁忽略了这个领域,他就没有走进耀州窑的心灵深处。”
歌谣寄托了窑工们美好的愿望,窑神是他们的图腾,是他们至亲至爱的庇护者,窑工们相信窑神,他们心中的窑神会保佑他们所烧的每一窑产品如玉,会给他们带来好运气。窑神不是实实在在的官府,不是皇差,不是窑主,不是地保,不会给他们板着脸催要税款,不会拿大牢和皮鞭吓唬他们。窑神的索取很简单,一只公鸡、一个猪头足矣,这些东西到头来还是进了窑工的肚子。所以,窑神终了只是精神的索取。
后来,还听这位老窑工吟诵了瓷镇陈炉关于陶瓷的一些歌谣:“金娃娃,银娃娃,顶不住咱这泥娃娃;金银棍,粮食囤,顶不住咱这搅轮子棍。烧瓮瓮来烧坛坛,又烧碗碗又烧盆,盆盆大得能坐人,碗碗能盛几桶水……”
“五月十三下一点,耀州城里卖老碗。”
老窑工说,5月13日要是下了雨,就意味着这一带全年风调雨顺,粮食丰收,可以放开肚皮吃饭,陈炉瓷户们就要去耀州城卖“老碗”了!我说:“有些地方咋说‘五月二十六下一点,耀州城里买老碗。’呢?”老窑工大笑:“关中道五月份下雨,都差不多,咱们卖碗,当然他们买碗了。”
民谣来源于土地,来源于生活,铜川是耀州窑的故乡,这些民谣如同耀州窑一样,在铜川这块土地上,壮硕而挺拔,睿智而多姿。
民谣是群众自己创作的,在群众中流传,语言自然无多讲究,长短不拘,可雅可俗,甚至口语化,是一种典型民间韵文文体。
譬如《我是我哥贤良妹》:“白石头,开白花,我是我父小冤家,我是我妈水仙花,我是我哥贤良妹。哥哥得病十八天,妹妹头上拔金钗。人人都说金钗可惜了,只要哥哥病痊好,打的金钗不戴了。”
铜川这块土地,属于广义的黄河流域,按如今的行政区划,地貌有点像个熊猫。熊猫头顶距人文始祖黄帝陵90余公里,和黄帝文化圈贴得很近。早在六七千年前,就有先民在漆、沮两河流域猎采牧耕,繁衍生息。说它历史源远流长、人文荟萃一点也不为过。这里,有以耀州塔坡遗址为代表的百余处新石器时代和商周时期的古人类聚落遗址;彭祖、阴康氏、孟姜女、鬼谷子的传说在这里广为流传;宜君县战国魏长城遗址被确认为世界文化遗产;秦、汉、隋、唐时期,这块土地属于京畿之地,受首都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境内留下了十分丰富的文化遗存和历史遗迹;唐代高僧玄奘曾在这里译经、弘法、创立唯识宗,并圆寂于此;这里诞生过西晋哲学家傅玄,唐代医药学家孙思邈、书法家柳公权、史学家令狐德棻,北宋山水画家范宽等一批哲人先贤,他们都为灿烂的中华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驰名中外的耀州窑在唐代就是中国陶瓷烧制的著名产地,窑火不熄,绵延至今;被称为“北山锁钥”“榆塞雄关”的铜川金锁关,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曾被认为是“关中四关”之一,历史上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传说和故事;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在铜川照金镇创建了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成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发祥地,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历史一路走来,民谣也一路走来。
譬如著名的药王山二月二庙会民谣,至今已流传千年:“二月二,人真多,药王爷,来施药,你治头,我治脚,一年到头笑呵呵;二月二,人真多,女坐轿,男坐车,听大戏,吃油馍,风调雨顺好生活。”
还有这首关于药王山的残缺的劳动号子:“……出东门,往东观,一下走到药王山,药王山,是宝山,青石台台有万千;进洞门,望显观,药王爷高坐在中间,龙君敬德站两边……”
照金革命根据地有一批80多年前的民谣,至今还能窥摸到时代跳动的强劲脉搏:
“升子借粮,斗子还粮,照金百姓心凉凉。打破升斗,分到土地,红军队伍向太阳。”
民谣中提到的升与斗就是照金老百姓常用的农具,大的叫斗,小的叫升,一斗能够装10斤,一升只能装4斤。地主借给老百姓粮食的时候用小升子借,还粮的时候要求必须用斗还。这样大进小出,老百姓苦不堪言,刘志丹的红军队伍给人们带来了希望:“刘志丹,走耀县,路过走的西塬畔,阴阳二河打过站,白家庄里扎营盘,杀富济贫把粮散,招兵买马闹红了天。”
这里的阴阳二河分别指耀州的阴家河村和阳家河村,白家庄也是耀州的一个村子。
这批民谣是最早反映照金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的文艺作品,需要重视并给予它们应有位置。
如所有的文学艺术作品一样,民谣也是来源于生活但又高于生活本身。它和它的创造者一样简朴,一样单纯,一样直面生活,不藏不掖,一样落落大方,透明真诚。它是从生活实践中提炼出来的,又反过来成为人民群众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
民谣从内容上来看,繁杂多彩,有礼仪歌、时政歌、生活歌、情歌、劳动歌、儿歌六大类。礼仪歌是民间祭祀祖先、欢庆节日、迎亲送朋、娶妻生子、哭嫁敬酒时唱的歌;时政歌的内容多是反映人们对政治事件以及各色人物的认识和看法,表现形式以针砭时弊和嘲讽居多;生活歌是反映人民日常生活和家庭邻里关系的歌谣,多含生活哲理,有指导和帮助的内容;情歌是民间歌谣中数量最多的一种,表达的情感十分丰富。有的抒发相思离别之苦,有的互诉忠贞,表明对爱情的决心,有的表明自己择偶的标准;劳动歌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别,广义的劳动歌是指劳动过程中唱的歌或者是为配合劳动而唱的歌,这些歌谣能够激励劳动者释放身体压力,调节情绪。狭义的劳动歌是指与劳动动作相配合的强烈的声音节奏,能够直接促进劳动生产;儿歌则诙谐幽默,朗朗上口,富含趣味,甚至俏皮搞笑。这些歌谣都折射出人们对生活实际和理想追求的直言不讳和艺术诉说。
百余年前,耀州川道附近水域盛产靛蓝,成熟后击捣成染料,于是就有了《打靛歌》:“屎巴牛呀拽碌碌呀,一下拽到洪水头呀,碰见一根大木头呀,腰里一摸是斧头呀,一斧头砍成两半头呀,把它搁到河里头呀,龙王见了愁心头呀,赶快行云遮日头呀,大伙心里凉飕飕呀。”
每一句后面众人都呼喊“噢呀啊哦嗬咳呀”,勇气和力量自然而然从土地拱出,慷慨激昂,声势浩大。
铜川煤炭开采历史很长,解放前铜川的小煤窑大都是私人矿主经营的,产量低,生产条件恶劣,矿工生命没有保障。矿工下井时基本上都是光着身子,头上顶一个鸡娃灯,手里拿一个洋镐,身后拖一个荆笆筐子,他们正月十五下井,五月端午升井;在地面休息几天再下井,八月十五再次升井;休息几天之后再下井,就这还要挨把头的皮鞭。民谣记录了这些场景:“大班窑,苦无边,一下就是百十天。窑工日夜在井下,当牛做马受熬煎。紧三鞭,慢三鞭,不紧不慢又三鞭。流不完的血,淌不完的汗,挨不完的鞭子,拉不完的炭。”
生老病死是生活常态,是永远的话题,宜君的这首《丧歌》别有意味,似乎说一方水土对人的哺育,又似乎说人生的必然归宿:“高高山上一口泉,流来流去几千年,人人都喝泉中水,愚的愚来贤的贤,我提壶来亡人饮,谁接壶来我交传。”
在民间歌谣这个大家族里,属儿歌最多,最深入人心。许多儿歌并没有什么道理,逻辑上也似乎不通,但细细品味,趣味和幽默是其重要特质,蕴含了人民群众对生活中万事万物的调侃和不断迸发的智慧。
如《老鼠娶亲》:“快到年里头,老鼠娶媳妇。媳妇叫花猫,长得就是嫽。它家住对面,隔着一座桥。媒婆是老牛,它给作介绍。老马驮彩礼,搬了一个槽。老羊是说客,提了一筐苕。黑狗当保人,来来回回跑。白兔来帮忙,放的红鞭炮。肥猪当大厨,把鱼油中泡。小龙搭彩棚,老虎帮抬轿。猴娃敲锣鼓,乌龟开大道。青驴吹喇叭,鸭鹅在放哨。娶回花媳妇,一窝老鼠笑。揭开红盖头,变成大傻帽。喵呜吼一声,胆破吱吱叫。娶回个煞星,从此哭祖庙。”
民谣细数,分“歌”“谣”两类。《诗经·魏风·园有桃》有诗句:“心之忧矣,我歌且谣。”《毛诗故训传》解释此句说:“曲合乐曰歌,徒歌曰谣。”即合于乐章,有一定的曲调、唱腔,并用乐器伴奏来演唱的是歌;没有曲调,但词句有较强的节奏感,以吟诵的方式来传播的是谣。
铜川民谣当然也具备这样的特点,1989年编撰而成的《铜川市民间歌谣集成》里,除纯粹的“谣”之外,就有若干可吟可唱的“歌”,如《十对花》《小拜年》《董家庙》《摘椒》等。
尤其《摘椒》曲调明快,活泼生动,流传于耀州小丘一带:“姐儿门前一树椒,怀抱着椒树去摘椒,两眼一个往上瞧;椒树股股长得弯,奴去摘椒挂了衣衫,没拿一个绣针连;椒树刺刺长得尖,奴去摘椒扎了手尖,没拿一个钢针剜。”这种综合性的艺术形式,不仅有富于韵律的语言,而且可合于乐曲用来演唱,演唱时还常伴以舞蹈。在古代,诗、乐、舞通常是三位一体的。《吕氏春秋·古乐》记载:“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它所描述的就是融诗、舞、乐于一体的艺术活动。
中国古代文学典籍《诗经》中的诗原本是综合性的艺术活动,《墨子·公孟》中就提到,在孔子时代的《诗经》有“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
铜川耀州西塬过去有一种婚俗,主婚人端一个升子,内盛石子、谷草等物,紧跟着新郎新娘转着圈且说且唱:
“先撒金,后撒银,再撒新人出轿门。”
顺次下来撒东西南北各个方位,依次而行。
还有一种婚俗,是主婚人点一把火,绕着新郎新娘舞蹈歌唱,一为祈福,二为燎去浊气:
“烧烧烧,燎燎燎,轿里坐个嫽宝宝,向上看,莫弹嫌,向下看,两点点,不烧了,不燎了,厨子把肉熬好了。”后来,诗、乐、舞逐渐分化成三个独立的艺术门类,其主要格局沿着各自的艺术方向发展,但在民谣领域,相互配合的情形仍比比皆是。
民风民俗十里九不同,铜川地形南接关中,北连陕北,民谣呈不同面貌,但大致相近,有一首《豆芽菜》,宜君一带说:
“豆芽菜,拄拐拐,常年在外做买卖,在外生意亏了本,腊月三十才回来。我在媳妇炕上坐,我妈骂我怕老婆。将心比心一个理,我爸当年咋爱你。”
而耀州一带则这样说:
“豆芽菜,拄拐拐,常年在外卖药材,生意不好难发财,腊月三十跑回来。媳妇给我暖暖脚,我妈说我爱老婆。叫声妈呀莫挑理,我爸当年也爱你。”
民谣如同草木,茂密繁盛,世世代代催生了许多优秀的民间艺人,如《铜川市民间歌谣集成》中记载的宜君的张福生、贺喜才、许启忠等,耀州的张贤根、杨义民、王明皋等,铜川老区的杨建成、严树林等。著名作家和谷的外祖父吴忠玉是王益区黄堡人,年轻时曾当脚夫赶骡马,一生勤劳乐观,正直善良,尤其喜欢唱歌,是方圆有名的秧歌伞头和民歌大王。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铜川市群众艺术馆音乐干部曾采访过他,留下了一批民谣,经和谷抄录修订的《十绣》是其代表作:“一绣天上一朵云,二绣王母赴蟠桃。三绣黄河水摆浪,四绣鸳鸯水上漂。五绣五龙来戏水,六绣金鸡展翅飞。七绣七星当头照,八绣八仙来过海。九绣九哥前边走,十绣金银一盒子宝。”
许多文学艺术工作者从民谣中汲取营养,著名的《唱支山歌给党听》的作者姚筱舟曾言,年轻时他经常和矿工们一起喝茶、拉家常,记录下许多矿工编的顺口溜和歌谣,从中受到启发,譬如这首:
“党是妈,矿是家,听妈的话,建设好家。”
细细辨识,《唱支山歌给党听》应有其基因。
时间在向前滚动,铜川的民谣还在继续吟诵,不久前,听到一首新民谣《新铜川谣》:
“铜川铜川,无铜有川,办事陕西,口音河南。喝酒干脆,不倒不算,一般不喝,不喝一般。民风淳朴,海纳百川,家风严谨,好人涌现。苹果樱桃,滴水欲馋,核桃蜜桃,秦椒大蒜。耀芪宜党,史传久远,娑罗圣树,战国城垣。水泥煤炭,享誉河山,贡献数年,资源枯干。经济转型,养生保健。耀瓷生辉,照金灿烂,香山佛光,玉华禅院。云梦道教,陈炉窑烟,一圣四杰,扬名立万,不尽乡愁,爱我铜川。”
品味再三,竟深入其中,有些不能自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