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铜川 | 历史意识与现代精神的相互激扬——吴铜运诗集《遥远的树》《夜之旷野》中的兴观群怨
历史意识与现代精神的相互激扬
——吴铜运诗集《遥远的树》《夜之旷野》中的兴观群怨
苏云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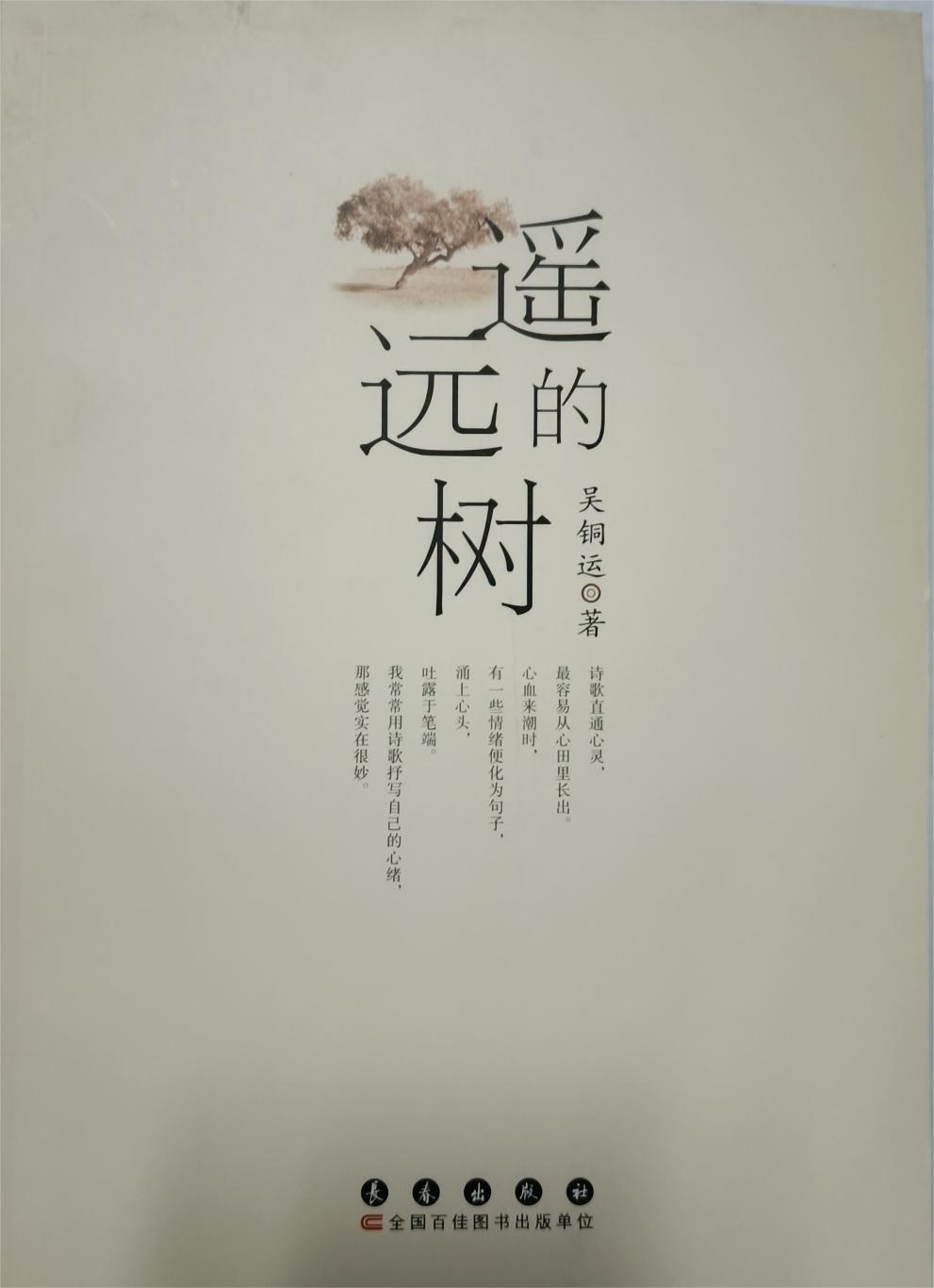

《遥远的树》出版九年后,诗人吴铜运又出版了《夜之旷野》。通读两部诗集,既能感受到诗人创作风貌的自然流变,又常常被诗歌中那坚实的内核和气韵所吸引。
那么,这些诗歌都有哪些堪称坚实的内核和气韵呢?
首先,吴铜运的诗歌创作所走的路子极正:兴观群怨,无不中矩,抒情言志,自然而然。他诗思如流水,随机而动,遭遇自我情绪则为自我情绪造型,遭遇身边人事则为身边人事画像,遭遇历史烟云则为历史烟云慨叹,遭遇时代万象则为时代万象抒怀。
创作风格上,他的诗歌恰如艾青所说“是以自由的、素朴的语言,加上明显的节奏和大致相近的脚韵作为形式。”因而,这些诗句既有朴素有力、宽阔明朗的写实力度,又不乏含蓄蕴藉、富有机锋的象征意味。
在总体风貌上,因其取材随机而动,其诗歌就显得既无“我执”,又无“法执”,既不沉沦在自我情绪的小天地里不能自拔,又不刻意追求某种新奇的技巧,以“炫技”来哗众取宠。他的诗句只是朴朴素素、扎扎实实、磊磊落落地写在纸面上,带着历史的厚重,带着清白的风骨,带着书生的意气,勾勒、描摹、铺排、诉说,在诗意流淌中呈现出情绪的浓度与思考的脉络,让读者随着诗句的节奏而心潮起伏。
诗集标题《遥远的树》和《夜之旷野》,本身就是诗歌风貌的典型代表。《遥远的树》朴素坚定,言约意远,画面感十足。该诗集中《倾斜的古榕》《火炬树》《美丽的夜晚》《小楼望月》等,都属此类。《夜之旷野》略微增添了一丝华丽,但也有着坚定厚实的气韵。该诗集中的《老屋》《殇(组诗)》《鱼化石》《日思·夜想》等,都具有同样的美学风貌。
吴铜运的诗歌已形成了自身辨识度,足以让人有所期待的。他的咏史诗、传统文化题材诗,在其历史专业出身的加持下,每一次落笔,平淡的句子背后都蕴含着力透纸背的历史底蕴和人文情怀。在与历史、人文元素的互动中,他的诗句古意盎然,有共振,有慨叹,有反思,有映照。
将吴铜运的诗分为三类品读,更容易理解其诗歌的内涵。
第一类是以现代诗为载体,进行重述或再演绎。如《遥远的树》中的《咏菊》《李白》《鸦声》《玄奘》《李后主》等,以及《夜之旷野》中的《汨罗江,打开一扇天窗》《金锁关怀古》《淮阴侯》《风雪夜归人》《在贺兰山,我静听一种粗粝》等。这些诗是诗人对特定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或历史元素,进行文学化、诗歌化或再文学化、再诗歌化的创造。它们不同于纯粹的历史,也不同于纯粹的古典文学,而是经历了一位现代诗人的诗意发酵,属于重述,属于演绎。比如说《咏菊》,这首诗很得古典诗精髓,但其用以营造“古典意境”和“古典意味”的语言和思维,却都是现代的。《李白》《玄奘》等诗的落脚点,则是在读懂古人、读懂古典作品的基础上,在历史长河和古代文人中寻觅知音。
第二类是注入了新内涵的重新阐释。如《遥远的树》中的《蝴蝶》《李白之恋》《精卫》《千人石》《苏州印象》等,以及《夜之旷野》中的《哭泉赋》《哀屈原》《商君书》《少正卯》《孟浩然》《前朝》等。这部分诗歌极见功底,它们不仅是审美化的艺术品,诗中更潜藏着诗人的种种感怀与思考的结晶,是诗人学养积淀和人生经验生发而来的,它们可以看作诗歌化的史论或文论。可贵的是,诗中的每一处论断,并不都是信马由缰的文学想象,而是有着丰富的历史现实基础和学理逻辑支撑。比如《走过秦直道的梦呓》中对秦朝功过的思考评判,对传统史书的质疑,就被睡虎地秦墓竹简等众多的考古成果所证明。我曾参与过吴老师的秦直道之行,亲历过《走过秦直道的梦呓》《秦直道仿古》《沮源关探幽》等诗歌的前期酝酿与激发过程,所以对他的此类诗歌创作尤为敬佩。此外,在这些诗歌中,《苏州仿寇慎遗存》是颇为特殊的存在。这首诗与其说是注入了新内涵的重新阐释,不如说它的产生是对诗人主观期待的一种回应。
第三类是戏谑与解构类。如《遥远的树》中的《闲戏孟浩然》《想杜甫》《周易》等,如《夜之旷野》中的《兰亭雅集》《饮荷》《夜读》等。这些诗歌其实是前两类咏史诗的特殊延伸,它们或是戏谑性的演绎,或是解构性的阐释。读这些诗,我们能够清楚地感知到它们只是套上了历史或典籍的戏装,借用了历史或典籍的道具,而其内核则根植于现实土壤,根植于我们眼前的社会万象。我尤为喜欢那首《松下问童子》。这首诗极端单纯,也极端复杂,它所依托的诗歌原本描摹了一个非常戏剧化的场景,诗人在再创作中又赋予了诸多演绎式铺垫,让戏剧色彩和诗意体验迅速攀升到极致。它似乎颇有些后现代的解构意味,但它在审美极致到达之前的笔触攀爬又显然是一种精巧的建构,它是一件同时具备单纯和复杂特征的精巧艺术品。
以上所说的这些咏史诗,无论是临渊凭栏的咏史,还是皓首穷经的咏史,都是对中华文脉的可贵延续,它们张扬着古典意蕴,焕发着现代精神。哪怕是那些戏谑的解构,它们背后的支撑也绝非是对猎奇扮丑的追求,而是杜甫“归来倚杖自叹息”式对社会公平正义、对人心和谐美好的深切呼唤。
那么,除了这些坚实的内核和气韵。两部诗集还展示了诗人创作风貌上的哪些变化呢?
我的观察是,诗人在《遥远的树》中展示出的极广的诗歌路向、多维的语言风格以及熟稔的调度能力,在9年后的诗集中呈现出了一种自觉的收缩态势。表现最为明显的是曾经多元、多维的诗歌朝着诗人最敏感、最擅长的咏史抒怀诗聚拢。在《夜之旷野》中,像之前《冬景》《第四代》这样颇具阿波利奈尔式的试验气质的诗歌消失不见了,像之前《写在继续教育考试后》《胆怯的爱》等极端口语化的诗歌也消失不见了。《夜之旷野》中,仍然有诸如《空城计》《新买的旧书》《我丢了一个U盘》《日子》等题材生活化、表达口语化的诗歌。
这样的现象是好是坏呢?它无疑说明了诗人的创作路向从粗放走向了集约,从自发走向了自觉,但是否暗示了现实生活的愈发苍白,而历史文化元素愈发诱人了呢?令人欣喜的是,诗人的探索并未停步。《夜之旷野》中出现了语言更为有力、如箴言般的《石头》,出现了《月亮坐过的石头还暖着》《我的诗被冻在眼泪里》等风格独特的诗,它们明显继承了唐诗宋词的古典意象,却因没有明确的古典文化指向,读来充满了现代气息。
最后,我注意到两部诗集中“树”的意象颇多,它们在《遥远的树》《倾斜的古榕》《火炬树》《阿里山神木》《孤寂》《河流》《夜之旷野》《南凹古槐赋》《西大记忆》《岁月感怀》等诗歌中,纷纷然以不同的形象登场,被赋予了不同的象征意义。它们象征着什么呢?我想,它们无疑象征着深深扎根大地的坚韧、孤独、沉默、无助的人们,包括所谓的胜利者、失败者,也包括我们深埋心底的呐喊和希望。



